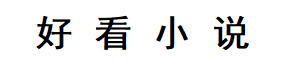说罢,我气呼呼地率先朝胡同口走去,他也不恼,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。到了那小饭馆,一进门,一股混杂着饭菜香和烟酒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饭馆不大,摆着几张有些油腻的木桌子,灯光昏黄,墙壁上糊着的墙纸都已经发黄剥落,露出里面斑驳的墙面,角落里还堆着些空酒瓶子,一看就是个有些年头的老地方了。
我俩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他扯着嗓子朝后厨喊了一嗓子:“老板,上酒,要最烈的那种!”老板应了一声,不一会儿就拎着一瓶酒和两个脏兮兮的酒杯走了过来,把酒往桌上一放,又转身去拿了盘花生米,嘟囔着:“悠着点儿喝啊,别又喝大了闹事。”
他也没理会老板的话,拿起酒瓶子,“砰”的一声打开瓶盖,往两个杯子里倒满了酒,那酒液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泽,看着就像一团燃烧的小火苗。他端起一杯,朝我举了举,说:“哥,之前的事儿对不住了,我这人嘴欠,这杯酒我先干为敬,算是给你赔罪了。”说完,一仰头,就把那杯酒一饮而尽,眉头都没皱一下,只是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,放下杯子,抹了抹嘴,看着我。
我冷哼一声,心里虽然还有气,但也不想显得自己小气,便也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,那酒一入口,就像一条火舌顺着喉咙直烧到胃里,辣得我直咳嗽,眼眶都被呛出了泪花。他见状,笑了起来,一边笑一边给我拍着后背,说:“哥,你这酒量可得练练啊。”
我瞪了他一眼,没好气地说:“少废话,今天非得跟你分出个高低来不可。”说着,我抢过酒瓶子,又给自己倒了一杯,再次仰头灌了下去。
这酒一喝起来,就收不住了,我俩你一杯我一杯的,也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杯。随着酒意越来越浓,我们的话匣子也渐渐打开了。我这才知道,他叫秦幽,今年才28岁,打小就没见过父母,是跟着师傅在这县城里长大的。说起他师傅的时候,他原本带着几分醉意的眼睛一下子变得通红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咽,说他师傅对他那是掏心掏肺的好,把一身的手艺都传给了他,可没想到,师傅在今年也去世了,这对他来说,就像天塌了一样。
他一边说着,一边用手抹着眼泪,那平日里看着冷漠又强硬的形象此刻荡然无存,只剩下一个失去至亲后满心伤痛的大男孩模样。我看着他,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,想起自己爸妈离世的事儿,眼眶也红了起来,忍不住安慰他说:“兄弟,我懂你的感受,我爸妈也刚走,这世上最亲的人没了,那种痛啊,真的没法说。”
他听了我的话,哭得更厉害了,尤其是想起之前那句不该说的“没爹妈教”的话,他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跟我道歉,说自己不是故意的,让我别往心里去,那懊悔的样子,让我心里的气早就消得一干二净了。
酒越喝越多,我俩的话也越来越多,我借着酒劲儿,把我之前那些倒霉事儿一股脑儿地全倒了出来,什么破产啊,老婆孩子走了,爸妈也离世了这些事儿。我边说边比划着,说到伤心处,眼泪止不住地流,声音也变得沙哑起来。他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,脸上满是同情和不忍,时不时地给我递张纸巾,或是陪着我叹口气。
这一顿酒,直喝到外面的天都黑透了,饭馆里的客人也都走得差不多了,只剩下我们这一桌还亮着昏黄的灯光。我俩都醉得迷迷糊糊的了,连怎么走出饭馆的都不太记得,只记得后来不知怎么的,就到了一家宾馆,进了房间,我一头栽倒在床上,就啥也不知道了。
等我再有意识的时候,已经是第二天了,我在宾馆的床上醒来,脑袋昏昏沉沉的,像被人用锤子敲过一样,疼得厉害。我眯着眼睛,好半天才适应了屋里的光线,伸手摸过手机一看,都下午6点多了。我点开通话记录一看,里面多了一个联系人,名字就是秦幽。我望着窗外那已经西斜的夕阳,那橙红色的余晖洒在窗台上,给这有些简陋的房间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暖意,可我心里头却一片空白,回想起这一连串的事儿,心里头那滋味儿,真是复杂极了,怎么也没想到,就这么和秦幽算是结下了这么一段奇特的缘分啊。
手机站全新改版升级地址:http://wap.xbiqugu.la,数据和书签与电脑站同步,无广告清新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