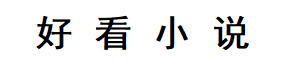出大事了!提刑司来了个女煞星! 第4章 情场老手(2/3)
“那老头眼睛毒得很。若是被他发现,告诉了映红楼里的妈妈,只怕我俩会被那老鸨子拿得死死的,当一辈子的摇钱树。”
牢房外传来了两声鸟鸣,天已经大亮了。小青看着自己手上的镣铐,只怕自己是再也见不到天光了。
“可我们真的没有在车上动手脚,或许是那花车本就构造复杂,陈老三没有造好。又或者......是天罚!”
谢含辞出了牢房,崔衙役立刻贴了上来。
“谢小姐,怎么样,都招了吗?还是叶师爷厉害,一张嘴一会儿是女人的啼哭,一会儿是哀嚎,若不是我在他旁边配合打板子,还真以为是动了大刑。”
“那叫口技,学着吧,深着那。”
谢含辞只觉得被这朝阳一照更加困了,上了马车,等她的却不是谢渊。
“王王.....王爷,好巧啊。”
天啊,她说了什么啊。
马车在这个时候动了起来。见宁王看着车窗外一言不发,谢含辞有些沉不住气了,便开口问道:“宁王,我们这是去哪?”
“回家。”
只有两个字,他还真是惜字如金啊。
什么意思?回谁家?他家不是在京城吗?还是他的意思是送她回谢府。
一路上他始终闭着眼睛,谢含辞如坐针毡,直到看见马车拐进了谢府的巷口,他又突然睁开眼,开口问道:“你手上可有沈画师的东西?”
“没有,没有。我在他生前从未见过他,他也没有送过东西给我。”
他看着谢含辞,不像是在说假话,轻咳了一声。
“有件事还是要跟你说一下,跟案子有关。沈画师,是我的线人,他生前一直在追查大越在蜀州城安插的细作,他手里有一份名单,藏在了平日往来的信件里。”
谢含辞没忍住:“王爷,你们对线人的人品是不是没有什么要求呀?他天天朝三暮四,您知道吗?”
宁王蹙眉:“线人有的时候需要逢场作戏,这也是不得已,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吗?”
谢含辞在死者为大和将他的破事抖出来之间横跳,刚想开口,突然想起了什么,“王爷,您刚才说什么?”
“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?”
“不对,是上一句。”
“线人有的时候需要逢场作戏?”
“对!”谢含辞对车夫喊道“改道,映红楼”。
二人到了映红楼,谢含辞却被告知元娘已经离开映红楼了。
龟奴揉着惺忪的睡眼,很少有来得这样早的客人,还是个女客。但在他看清是谢含辞后也就不奇怪了。
蜀州女煞星,就是阎罗殿她也是敢闯一闯的。
“昨晚她受了伤,红妈妈说要给她请大夫,但她却一副丢了魂的样子,也不说话。回了屋子,拿出了一箱子的银子给红妈妈,说自己害了人要遁入空门,头也不回地往庵寺去了。”
谢含辞追问道:“哪个庵堂?”
龟奴思索了一会儿:“叫什么贞洁观,好像是这个名字。我还挺诧异,当了半辈子婊子,去什么贞洁观?”
是城郊的箴觉观。
谢含辞再次跳上了马车,她看着一同坐在马车上的宁王,刚想说点什么,肚子却先叫了起来。
“咕咕咕——”
谢含辞倒也不似寻常女儿家般不好意思,而是在车上大翻特翻,口中嘀咕:“怎么连块点心都没有。”
宁王从怀里掏出了块帕子,一打开,里面竟是半块胡饼,“行军打仗,留下的习惯。”
谢含辞也不客气,道了声谢,边吃边聊了起来。
“王爷你可帮了我大忙了,我就觉得这花车不可能自己就炸了,可是那对姐妹已经认下了杀害陈老三,没必要在沈画师的事情上再说谎。我刚才听你说,逢场作戏,一下想起来,那妹妹说起过自己和元娘曾一起沈画师和她姐姐......”
马车颠了一下,谢含辞险些被胡饼噎住,她连忙喝了口水往下顺了顺,接着说道:“沈画师确实是逢场作戏,但却是为了气那元娘。他对那舞妓忽冷忽热,无非就是想通过那人,勾起元娘的嫉妒心。你这线人,还真是个情场老手。”
宁王看着眼前不过的女子,不过十四五岁的样子,怎么在男女之情上有这么多见解。
“谢小姐,已有婚约了吗?”
“没有呀。怎么了?”
谢含辞眨了眨眼,不知他为何突--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