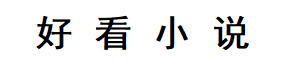娘亲!比咱老朱家某些……”
他顿了顿,似乎觉得不妥,目光扫过下面站着的几个儿子,尤其在某几个脸上掠过,哼了一声,才继续道,“……某些糊涂爹强多了!咱标儿、老四他们能有今日,还不是你这当娘的功劳?”
朱标闻言,脸上露出温和谦逊的笑意,微微躬身。
朱棣则嘴角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,目光复杂地再次投向光幕中那个跪地的小小身影。
马皇后轻轻拍了拍朱元璋的手臂,温言道:“重八,慈严相济方是正道。这位李贵妃心系社稷,其志可嘉,只是对孩子…也忒严苛了些。”
朱元璋不以为意,大手一挥:“严点好!那是龙种!是未来的皇帝!不严能行?咱看他学得挺好嘛!五岁就能读书,比咱当年强!哈哈!”他畅快的笑声在广场上回荡,似乎对未来这位曾孙的早期教育颇为满意。
光幕并未因洪武皇帝的赞赏而停留,画面流转间,色调骤然变得沉重而压抑。
时间再一次跳回至隆庆六年五月。富丽堂皇的乾清宫寝殿弥漫着浓重苦涩的药味,宫灯的光芒似乎都被这垂死的气息压得暗淡了。
镜头推入寝宫东暖阁。明穆宗朱载坖,这位登基仅六年的年轻帝王,此刻形容枯槁地斜倚在明黄锦缎的御榻上,面色灰败,呼吸急促而微弱。
御榻边,垂着一道半透明的纱帘,帘后隐约可见皇后陈氏与皇贵妃李氏(此时已因太子生母身份而晋封贵妃)的身影。
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,穿着一身略显宽大的素服,小脸绷得紧紧的,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惶恐和茫然,肃立在御榻右侧,双手紧紧攥着袍角。
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传来。三位身着绯袍、神色凝重的大臣被司礼监太监冯保引入暖阁。
为首者须发半白,面容刚毅,正是内阁首辅高拱。其后是面容清癯、眼神深邃的次辅张居正,以及年事已高、面带悲戚的阁臣高仪。
“陛下……”高拱抢前几步,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哽咽,跪倒在御榻前。
病榻上的隆庆帝艰难地睁开浑浊的眼睛,目光费力地聚焦在高拱脸上。他枯瘦如柴的手,颤巍巍地从锦被下伸出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死死抓住了高拱的手腕!那冰凉而枯槁的触感让高拱身体一僵。
“先生……”隆庆帝的声音嘶哑微弱,如同破旧的风箱,每一个字都带着浓重的喘息,却蕴含着一种托付江山的千斤重担,“朕…朕不行了……这…这江山社稷…太子年幼……全…全靠先生…劳…劳累了……”他死死盯着高拱的眼睛,仿佛要将所有的嘱托和未尽的不甘都刻进去。
高拱老泪纵横,反手紧紧握住皇帝冰冷的手,额头重重磕在御榻前的金砖上:“陛下!老臣……老臣肝脑涂地,必不负陛下所托!必不负大明江山!”张居正、高仪亦随之叩首,泣不成声。
隆庆帝似乎耗尽了最后的气力,抓着高拱的手缓缓松开,头无力地歪向一边,眼神开始涣散。
冯保上前一步,尖细的嗓音带着一种程式化的悲戚,展开一卷明黄诏书,声音在压抑的寝宫里异常清晰:
“遗诏,与皇太子。朕疾弥留,殆弗可兴。皇帝你做。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。尔要依三辅臣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并司礼监冯保辅导,进学修德,用贤使能,无事荒怠,保守帝业。钦哉!”
“进学修德,用贤使能,无事荒怠,保守帝业!”
这十二个字,如同洪钟大吕,响彻在寝宫,也响彻在洪武十三年的奉天殿上空。
三位阁老以头触地,泣不成声。帘后的李贵妃紧紧咬着下唇,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,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
十岁的朱翊钧看着父皇渐渐失去神采的脸,听着那关乎自己未来命运的重托,小脸上血色褪尽,身体微微颤抖。
“高拱…张居正…高仪…还有那个阉人冯保……”
朱元璋眯起眼睛,鹰隼般的目光在光幕上那四个名字上来回逡巡,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龙椅扶手,发出沉闷的“笃笃”声。
奉天殿广场一片肃然,所有人都屏息凝神,等待着这位开国皇帝对未来的“顾命班底”做出评判。
“高拱此人,前面天幕提过,”朱元璋缓缓开口,声音低沉,带着一种洞悉世事的锐利,“整顿边事,驱除俺答,是个能办实事的干才。让他为首辅,辅佐幼主,倒也算人尽其才。”
他的目光陡然锐利如刀,狠狠刺向张居正的名字,鼻腔里发出一声重重的冷哼:
“哼!至于这个张居正嘛……
心术就未必那么正了!咱记得清清楚楚!
嘉靖龙驭-->>